周信芳生活照
湛湛青天竟可欺?——周信芳談片
只記得他綽號叫「麒老牌」。先認得「麒老牌」,後才知道有個「麒派」。
別說,還真有點像,都是胖嘟嘟的四方臉。在那個時代,像「麒老牌」這樣的胖人真是個稀罕物,於是胖,也有了一個優雅的名詞:富態。不像現今,明明瘦成一把骨頭,還哭著鬧著要減肥。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傳統戲剛剛開禁,那時的戲迷能哼哼一段《空城計》都會讓人側目,而聽到《碰碑》的時候更加感喟,像我這樣聽慣高亢激昂、鏗鏘有力的「樣板戲少年」,從來不知道京劇居然也有如此悠揚輕緩、一唱三嘆的調子。
戲迷們經常湊在一起娛樂,「麒老牌」是常客,嘴一張就是《打漁殺家》、《宋士傑》,特別是唱《徐策跑城》,從「湛湛青天不可欺」開始,唱著唱著便進入劇情,學著劇中情景,在狹小場地上跑上幾步,這一跑,「麒老牌」的「富態」模樣不見了,臉上的胖肉一顫一顫,一會便上氣不接下氣,多出了幾分好玩、憨態。
麒老牌在戲迷中頗受歡迎,人緣不錯,笑起來憨憨的樣子。事隔多年,聽說「麒老牌」去世了。人老了,總歸有這一天。
文革十年,可謂恍惚,可能戲迷們早就忘記京劇行腔原理,嗓子啞就是麒派,得了重感冒就可以唱裘派了。其實「麒老牌」唱的並不很像,他那有點沙啞的嗓子是憋出來的,我也會點。他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唱麒派的人很少,能唱好的就更少。麒派的特殊嗓音和腔調,一開口非麒派莫屬,不像馬派、楊派,總要聽一會才能分辨出。唱得最像麒麟童的是誰?是周信芳。麒麟童就是周信芳。藝名。
那就說說周信芳吧。
周信芳,1895年生於江蘇清江(今淮安),籍貫浙江慈溪。填寫籍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知道別的國家是否有這樣習俗,而我們填寫籍貫到底是為了說明什麼?是對八竿子打不著的祖先的緬懷還是對故土的追念?以我數十年填寫籍貫的經驗證明:全無干係。至多滿足某些部門窺探個人隱私的慾望,當然,也能局部地滿足後人對祖先的攀附,比如孔門後代某教授,誰也阻擋不了他躺在孔氏家譜上的榮耀。
周家在祖籍慈溪曾經望族,只是家道中落,到了父親周慰堂只能在布店學徒,因他酷愛京劇,下海入了戲班。戲班是要四處遊走演出的,遂跟著戲班到了清江演出並結婚生子,這就是周信芳。如此一說,周信芳唱戲也是家傳。只是那時伶人地位低下,周慰堂「下海」之舉,引得周氏家族極為憤怒,於是把周慰堂及其子孫革出祠堂。周信芳身世尚有別傳,這裡只取其一。
既生伶人之家,耳濡目染,京劇對周信芳影響極大,不過五六歲許,小小周信芳就習得好幾出戲,七歲登臺,遂得藝名:七齡童。這一登臺,便技驚四座,令人讚嘆不已。
周信芳天賦極高,又身在梨園,多得名家真傳,迅即紅遍江浙滬,只是「七齡童」的名字不能再用,已超過七歲,於是更名「七靈童」,十二歲時上海演出,因海報誤植為「麒麟童」。從此,京劇界風生水起,周信芳以「麒麟童」名滿梨園,「海派京劇」呼之欲出。
此後,周信芳進科班「喜連成」搭班學藝,認識了梅蘭芳並同臺演出。而對他影響頗大的是名伶金月梅,因為能演許多新戲,周信芳對新編劇目尤為偏愛。當他十五歲時,因嗓子「倒倉」,不能再像其他演員一樣揮霍嗓子,這對戲劇演員原本不幸,可周信芳卻能悉心專研,博採眾長,兼收並蓄,不僅研習舊戲,在表演和編戲上投入更多。這一逼,逼出一個「麒派」。1928年「麒社」成立,麒派誕生。
周信芳正好出生在上一個世紀之交時期,那正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動盪時代。作為京劇藝術家,他顯然受到時代變革的影響,算得上「熱血青年」,當代則有「憤青」一說,只不過是語言的激憤,不僅缺乏行動本領,連認識社會的眼光也不具備,更易受世俗誘惑,施以小利,立刻繳械投降。周信芳卻是身體力行,反映在藝術生涯中就是對新編劇目的強烈熱愛,而他對時代的變遷總是不乏敏感:宋教仁遇刺,他就編演《宋教仁》;袁世凱稱帝,他演《王莽篡位》;「二七」京漢鐵路罷工,他演《陳勝吳廣》;「九一八」事件爆發,他編演《滿清三百年》,逐漸自覺意識到戲劇也要反映「人間意志的爭鬥」。抗戰爆發,身陷孤島上海的周信芳所演劇目又總與「抗敵」有關,如《徽欽二帝》、《明末遺恨》、《梁紅玉》等等。但這並不意味著周信芳具有準確把握政治風雲的天才,不過一個有良知藝人對社會狀況的本能反應,到了文革,良知失效,「本能」麻木,怎麼也趕不上時代步伐。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周信芳就與田漢交往,1927年加入田漢主持的「南國社」;1932年5月第一次淞滬戰爭以後,周信芳成立「移風社」;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移風社」東山再起,不論演藝生活和社會活動,周信芳左翼色彩濃烈。上海淪陷期間,他表現出強烈民族大義,與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地下組織多有往來,是當時京劇界進步力量的重要代表。
抗戰結束後,1946年初秋周恩來在上海思南路107號周公館與周信芳初次會面,周信芳與中共關係愈加密切,國民黨潰敗後,他堅守上海而沒有移居香港。
1949年中共建政,由於周信芳在京劇藝術上的傑出貢獻,出席了第一屆文代會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當選全國文聯文委、全國劇協常委,戲劇改進會負責人,稍後又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這一榮譽,京劇界鳳毛麟角。
周信芳早慧,成名早,走南闖北,早就蜚聲梨園,他多次目睹、並親身領教過藝人被壓迫、被欺凌的事件。新政府給周信芳待遇優厚,一系列重任都壓到他身上:上海戲劇改進協會京劇分會主任委員、上海市文聯常務理事、上海市文化局戲曲改進處處長、華東戲曲研究院院長,周信芳極重情義,知恩圖報,在新政府領導下,他果然不負眾望,對工作十分投入,而且成績斐然。抗美援朝期間,不僅新編、演出歷史劇《信陵君》,還多次為志願軍發起義演,用以購買戰鬥機。周信芳愛國之心可謂拳拳。
1955年周信芳出任上海京劇院院長,在京劇界地位日益提高,毛澤東、周恩來都看過他的演出,周信芳也日益繁忙,出訪、演出、行政,忙的不亦樂乎,並於195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看了一出有「海瑞」角色的清官戲,於是要求有關部門找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寫點文章。會後,□□部的兩位副部長,胡喬木回北京找吳晗寫了幾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吳晗後經馬連良要求搞出了《海瑞罷官》的劇本;周揚則在上海請周信芳編演《海瑞上疏》。周信芳畢竟藝人,一個懂得感恩的藝人,黨給了他很高待遇,他對黨安排的工作自然毫不怠慢,何況早年也演過《海公大紅袍》、《海瑞參嚴嵩》這樣的「海瑞戲」。《海瑞上疏》的劇本由許思言執筆,周信芳兼導演和主演一身,經過半年編排,被列為上海「國慶十週年獻禮」劇目,於1959年9月30日隆重首演於天蟾舞臺。這要比《海瑞罷官》早了一年多。
「海瑞戲」的上演確有一定政治考量:歷經1957年反右之後,許多人噤若寒蟬,不再敢開口說話,演「海瑞」只是鼓勵大家繼續「說真話」,表現他不畏強暴,為民請命的精神,完全沒有後來所批判的「為彭德懷翻案」意圖。安排這項工作時候,「廬山會議」尚未召開,彭德懷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這些藝術家們哪有未卜先知為彭德懷翻案的本領和膽量呢?
誰也沒有料到,「海瑞」這個死了三百八十年的歷史人物會掀起中國當代史的驚濤駭浪。
時代在以一種令人目眩的速度變化,像周信芳這樣從另一個時代過來的人,雖然不懂,但也照樣緊緊跟隨。
隨著「大寫十三年」號召,藝術家們紛紛投身於現代戲的創作中,周信芳此時已年近七旬,但他怎麼也不甘落伍,1963年下半年,為迎接全國現代戲會演,他主演了現代京劇《楊立貝》。可就在周信芳把這齣戲演繹到幾成經典的時候,卻接到「上級通知」,這齣戲不准上演,因為「楊立貝」是富農,周信芳藝術生涯中的最後一個角色就此夭折。取而代之的是《智取威虎山》。
1964年春,周信芳和夫人裘麗琳在觀看《智取威虎山》彩排,江青蒞臨。江青與裘麗琳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老相識,可裘麗琳哪裡能理解,此時江青早就不是彼時藍蘋,和江青見面時她脫口而出:「我們已經有好多年不見了。」一句話,使江青臉色大變。裘麗琳一句正常的招呼,卻如周信芳拿手名劇《徐策跑城》裡的戲詞:惹下了塌天大禍災。後來,江青對周信芳再無好臉色,表示自己怎麼能與周信芳這樣的人坐在一起?她也這樣說過童芷苓:「與童芷苓在一個黨內,我感到羞恥!」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關於「樣板戲」的問題,這是明的。暗中卻在醞釀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關聯,但周信芳肯定不知道,藝術家的心機怎麼也高不過政治家的謀略。周信芳再「進步」,也依然要按照「藝術規律」辦事,他反對在現代京劇中給主要演員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周信芳是京劇院院長,要按劇團管理規則辦事,又反對整個上海京劇院停下所有的戲碼,只搞《智取威虎山》這一齣戲。可這些「意見」卻不符合「革命需要」,政治家有自己的規律,周信芳的這些意見簡直就是文藝革命的絆腳石。
是絆腳石就要被踢開,周信芳大禍臨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且加了編者按。《海瑞罷官》的海瑞是馬連良主演,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中的海瑞,既然都是海瑞,那就一鍋端吧。正文是這樣寫的:「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個字後面是第15條註釋,註釋頗長,大意是介紹《海瑞上疏》創作、演出前後的情況。
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做的事。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前後寫了七八個月,多次通過秘密渠道進京修改,據說毛澤東親自改了三稿。
當年,不是說好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麼?於是京劇藝術家們拚命地推,結果,推出了一株大毒草——這正是姚文元文章所作出的政治判決。
這一劫,周信芳怎麼也躲不過了。
南周北馬,一個演《海瑞上疏》,一個演《海瑞罷官》,一南一北,遙相呼應,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轟出,倒下一片,如此節儉戰法,實乃用兵之道。或許有人問,一篇文章會有如此大威力嗎?我寫沒有,姚文元寫就有;寫在這個時代不一定有,寫在那個時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軀如何抵擋得了專政機器?馬連良於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馬連良年長,生命力也比馬連良頑強,當然,也揹負了更多的痛楚。
說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細拜讀過,真是才氣逼人,立論、駁論、結論,抽絲剝繭、層層推進;分析透徹、調理清晰;絲絲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氣、才子氣撲面而來,堪稱文章典範。可好文章全沒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處,這就是戮心。他的立論、駁論、結論,都是為了證明一個從來不存在的事實:為彭德懷翻案。時隔四十餘年,文革歷史早就被中央徹底否定,姚文元負罪入獄,也已病故多年,「戮心」之衣缽卻被完美繼承,不久前我就看過一位鬥士掛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訪談,每個字都含機鋒——不,是刀鋒,字字奪命的刀鋒。倘若此文寫於文革,被他「批判」的那家報社估計要從此墜入十八層地獄;倘若姚氏不死,定會翻身拜他為師。所幸,我們處於一個相對開放時代,盲從已不再是所有人的選擇,是與非、醜與惡,我們懂得。
戮他人的心,終將刻下自己的恥。魯迅曾云:搗鬼者有術,也有效,然以此成大業者,古來無有。
姚文元文章的威力,對待周信芳、馬連良、吳晗太過浪費,對待彭德懷也頗有盈餘,這些都不是文章的最終目標,在這篇看似四平八穩、才華橫溢的論文下面,潛伏著一條激盪的河流,半年之後翻捲成中國歷史上的駭人巨浪。
跟隨姚文元文章後面接踵而來的是批判周信芳的文章,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署名丁學雷文章:《〈海瑞上疏〉為誰效勞?》;5月26日接著發表署名方澤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到了6月份,對周信芳的批判已經連篇累牘,他從此墜入深淵,開始了地獄般煎熬。
上海京劇院是文革的重災區,八個樣板戲中的六出與上海有關,周信芳側身重災區,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歷史問題、現實問題都無法逃脫。文革中一系列標誌性懲罰統統落到他的身上,檢討、交代、抄家、批鬥、牛棚、遊街,無一倖免。
恐怖政治最恐怖的地方在我看來是對生活的直接干預,它肆無忌憚地闖入個人生活領地,不論你小心還是不小心,隨時都可能成為專政的對象,這在文革則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不但可以干預你的現實生活,還能干預你的歷史生活。給周信芳這樣的社會名流找點罪名不是手到擒來麼。比如周信芳和上海灘幫會頭子黃金榮、顧竹軒的來往,給漢奸吳思寶唱堂會。這樣的「罪過」,非但不是平常無奇,簡直就是罪不可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個時代,上海的舞臺都由這些「聞人」把持,周信芳不去那裡唱戲如何生存?給吳思寶唱堂會則是被槍押著去的,更如何讓一位藝人掮起國家淪陷的責任?周信芳是個藝人,一個深懷大義的藝人,大義上,他已經盡到自己的能力。
但革命家們的信念是極其純粹的,革命意志是不考慮環境、歷史和社會特徵的,自己革命,也要別人一樣革命;自己純情,也要別人同樣純情。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歷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別人的歷史——這對周信芳而言只是一種生活,只要生活在那個時代,都可能遇到這樣的經歷。
生活成了一種罪。
江青對童芷苓、對周信芳的態度都與其上海的經歷有關,正如裘麗琳所說的那樣:「她是藍蘋……我們本來是認識的……」是啊,三十年代上海灘藝人們認識藍蘋的不是一個兩個,但此時,她不叫藍蘋,叫江青,藍蘋是歷史,是一段需要用專政手段掩蓋和抹去的歷史。為此,江青煞費苦心。
插一段與之相關的故事。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發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被同時抄家的童芷苓、趙丹、鄭君裡、陳鯉庭、顧而已五家,本來這個名單上還有周信芳和於伶,合計七家,沒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為他在文革甫一開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紅衛兵抄過多次,且一直有紅衛兵把守;沒有抄於伶的家,則因為他家住空軍招待所對面,而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來自空軍江騰蛟手下。抄家原因,從他們的名字就能看出,無不是三十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與江青有過交往。江青自己沒有出面,通過葉群安排了江騰蛟手下去執行,他們對抄家人員要求「絕對保密」,並且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材料、資料。後來,抄出這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在江青親自監督下,由葉群、謝富治親手銷毀——這些東西留下了江青——還是藍蘋時期在上海的印記。1967年11月26日,張春橋親筆批示,18名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人士分別被拘留和隔離審查,他們紛紛成為「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軌線修理車上全市遊街示眾;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統「文革領導小組」在上海雜技場聯合召開文化系統各造反組織的「打倒周信芳」電視鬥爭大會——此時的電視,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稀罕物,這「最先進」的技術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在1968年4月25日批判賀綠汀時用的也是這一招。
我問過父親,可知當年批鬥周信芳麼?答:知道,鬥得可憐啊!再問:如何可憐?答:忘了。答的乾脆,忘的利索。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再殘酷、再荒謬都會被輕而易舉地忘卻,當真,我們是個容易健忘的民族?勒在歷史肉縫裡的那道繩索,怎麼能夠輕輕忘卻?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獄,一年之後被釋放。他的災難還禍及家人,兒子周少麟兩次入獄,孫女玫玫被嚇瘋,夫人裘麗琳因驚嚇一病不起,在周信芳尚在獄中時去世。這些橫禍都沒有換來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七十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問題上,張春橋明確表態:「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麼我張春橋就是反革命了。像他這樣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干」,「對周信芳,不槍斃就是寬大處理了」,怨毒深矣。這樣的表態真叫周信芳永無出頭之日——1974年秋,雖已文革末期,周信芳卻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給群眾監督。」——如果說這是周信芳「罪有應得」,那就是他至死也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徐景賢說:「像周信芳這樣的人,是一定會把花崗石腦袋帶到棺材裡去的。」
真是條漢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這位創作、改編、整理、移植劇目達二百餘出,其中堪稱經典的劇目就有幾十出,為中國京劇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藝術大師含冤去世。
湛湛青天,飄蕩著周信芳一縷冤魂。
周信芳《追韓信》劇照
周信芳《四進士》劇照
周信芳《徐策跑城》劇照
- 關鍵字搜索:
- 京劇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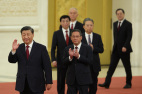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