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配圖(網路圖片)
【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第一章 當代英雄史詩
——藏人艱難並高貴在不相信英雄的時代
時間本無意義,是人的意志賦與時間意義,就像命運給了人靈魂。英雄史詩則是生命意義的華彩篇章。」
「當代,心靈腐爛於物性貪慾,精神之光黯淡;物性實用主義哲學成為生命意義的主題,理想主義如秋風中的黃葉飄零——這是一個背叛美與高貴,詛咒詩與英雄,並只懂得表述庸俗的時代。或許命運也厭煩了那令白玉之骨和鐵石之心都生出斑斑霉跡的庸俗,從而引導一個高原族群,在這個不相信英雄的時代,用血和淚書寫英雄史詩。」
「人類萬年歷史中發生過許多次民族大遷徙——為生存,為追逐豐美的水草或者財富,為逃離貧窮、奴役或者戰亂而遷徙。唯有藏人,是為了心靈的信仰和民族文化的獨特之美不被鐵血強權滅絕,才踏上悲愴的流亡之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達賴喇嘛尊者,引領八萬藏人,翻越萬里雲海之上的喜馬拉雅冰峰雪嶺,拉開當代藏民族流亡與遷徙命運的序幕:流亡,是為了信仰的自由;遷徙,是相信終有一日,能懷著聖潔的信仰,重返祖先的靈魂歡歌或者悲嘯的家園。」
「藏人的流亡與遷徙,已成當代的英雄史詩;這首藏人的命運吟誦的英雄史詩,越過半個世紀,依然迴盪在歷史中。藏人的流亡和遷徙,是通向蒼天的命運之路。連太陽都在物性貪慾中腐爛的時刻,由藏人的白骨與血淚鋪成的命運之路,正堅守精神的啟示;達賴喇嘛尊者在珠穆朗瑪峰巔,那塵世的極致之處,為人類不死於物性的庸俗,點亮一盞心靈的金燈,這或許是人類得到精神救贖的希望。」
「是的,藏人已經證明,並繼續證明自己屬於英雄史詩的族群… … 。」
金聖悲在一個僅可容身的高崖岩洞內思索當代藏人的英雄史詩。從他端坐沉思之處,可以俯瞰下面漫長的雪谷。流亡的藏人大多都要經過這個雪谷。半個世紀以來,藏人的流亡從沒有停止,就像高原上那永遠不停的風——每一個流亡的藏人,都是一縷染血的風。金聖悲所處的淺淺的岩洞,最初是鷹的棲息之所,後來被一位苦修者佔據。整整四十多年,苦修者在這個岩洞中為翻越喜馬拉雅的同胞祈禱,直到生命枯竭。牧民告訴金聖悲,因為神佛佑護,巡邏的大兵都看不到苦修者。哲人卻相信,真實的原因在於,苦修者枯槁似鐵的容顏同岩石的色澤極其相近,士兵從遠處看來,會把苦修者當作一塊黑石。
「數十萬藏人艱難的足跡曾走過這個雪谷,可是,只須一場風雪,一個民族走向心靈的足跡便被抹去,就像時間能令歷史虛化。」金聖悲在思想中感到了命運的冷酷。半個世紀來,藏人踏著虛幻的時間和深深的白雪,行進在流亡之路上。流亡者有像高原上的草木花石一樣自然的普通牧人,也有尊貴的法王和袈裟似火的僧人;有高級知識份子、剛畢業的大學生,也有只能聽懂風的歌聲、讀懂蒼天啟示的文盲;有雙眸如星的少年、花季的少女、剛毅的男子漢,也有衰朽的老人和朝霞般的兒童。社會背景和生理狀態如此不同的人群,竟會走上同一條命運之路——這是奇蹟,也是一個困惑。活著的流亡藏人的數目有「十餘萬」,但是,死在流亡路上的可能更多。
開始探尋藏之魂的最初歷程中,金聖悲時常向藏人提出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流亡?」但是,他卻很少能得到明確的回答。金聖悲曾以為,由於流亡凝結了太多悲苦和深情,以致於藏人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漸漸地,從藏人有些厭倦的注視中,金聖悲意識到他的問題是愚蠢的——有誰能回答浩蕩的風為什麼要湧過鐵褐色的荒野?只有完全不理解藏人,才會提出那種問題,或者說理解了,就不會再那樣提問。其實,只要向臉形如鷹如豹的僧人的眼睛注視片刻,就會理解藏民族為什麼流亡——一個以心靈的信仰作為生命意義的民族,怎麼能生活在崇拜物性的鐵血強權之下。
不過,無論原來有多少不同,只要走上翻越鷹也難以飛越的喜馬拉雅之路,就都會面對同樣的艱難。那種艱難屬於血淚和白骨;對於藏人,流亡首先是一次踏著死亡的鋒刃理解生命的精神歷程。金聖悲以乾肉充飢,以白雪解渴,以烈酒禦寒,已經在岩洞上端坐了一日一夜。他本想進入理解生死的哲學意境,但是,昨夜他卻領略到驚心動魄的悲情。
高原的暗夜,藍得發黑的天空令人恐懼。雖說哲人是超越恐懼的族類,金聖悲仰望夜空時,仍然感到了心的戰慄。藍得發黑的天空彷彿一個宿命的預言:人最終將歸於永恆的死寂,像一片冰冷的灰燼。那一刻,金聖悲萬念俱灰,百思齊滅,想讓自己的心,那團風中的紅焰,凍結在白雪中。然而,悽厲、高亢的呼嘯驟然撕裂了哲人的絕望。那在深邃的夜空中飛旋迴盪的呼嘯像是雪山的悲歌,又像是大地深處傳來的雄烈鬼魂的咆哮。震盪在呼嘯中的悲情,熾烈得能燒紅頑石,能點燃鐵鑄的絕望。金聖悲第一次感受到,大雪山原來也有生命,否則怎麼會在暗夜中發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呼嗥。
「藏人流亡命運的主題之一,便是能燒紅頑石、能點燃絕望的熾烈悲情!」金聖悲紅焰的心感到了璀璨的痛苦,一幕幕藏人翻越雪山的景象從他的意識中湧現。
一位決意為西藏獨立而作鐵血之戰的青年告訴金聖悲,他翻越雪山時,看到一個年輕的尼姑凍死在齊腰深的雪裡,她的臉形很美,可臉色卻現出猙獰的紫黑色——那種美和猙獰重疊的感覺幾乎讓他發瘋。這位青年還看到一頭凍死的氂牛,祂倚岩壁而立,背上的筐裡,有一個凍死的嬰兒。雖然只向嬰兒看了一眼,但是在那之後的一路上,青年覺得每一個黑色的石塊都像那個嬰兒的頭顱。
一位如同金燦燦的麥粒一樣豐滿的姑娘告訴金聖悲,翻越雪山時,她的一位女伴嘴和鼻腔中突然噴出一陣血霧,然後就凍死了。死前她竟然從懷裡掏出一朵小黃花——那是臨行前她從家鄉的雪水河旁採擷的。「我也不知道她想讓我幫她作什麼:是幫她把花兒戴在頭上,還是讓花蘸上她的血,等將來我回家時,幫她把花也帶回去… … 她噴出的血紅艶艶的,比陽光下的白雪還晃眼。… … 我該幫她作什麼?」當時,那位姑娘對金聖悲如是說,不過,她又像在問撩亂她黑髮的風。
姑娘給金聖悲看了她虔誠保存的那朵高原之花。花像聖物似的放在一個小小的銀盒內;失去生機的花現出憔悴的枯黃,只是花瓣間的幾絲殷紅仍然色澤明艶——那定然是死者血的遺蹟。凝視乾枯的花,金聖悲想道:「當西藏自由之後,這朵花會被帶回她曾盛開的故土;當那一天到來時,蒼天定會降下血雨,哀悼這朵花的命運。」
一位長著羚羊般善良眼睛的青年告訴金聖悲,他們二十八個人結伴流亡。穿越邊境的山口之前,他們用塑料袋把身體包裹起來,然後蓋上白雪,只露出呼吸和觀察的小孔,度過漫長的白天,以躲避中共的巡邏隊。太陽落山後,他們看到十幾個剛接近山口的尼姑被中共巡邏士兵發現。士兵開槍射擊。子彈劃出藍瑩瑩的光線,射進尼姑的身體:尼姑站著時,僧衣像火;倒下時,僧衣像一片血,彷彿白得發藍的雪地流血了。為救助還沒有被打死的尼姑,藏在雪下的二十八個藏人幾乎同時站起來。士兵們在震驚中停止了射擊,並衝上來用槍逼住藏人。士兵只有五個人,其中一個用步話機向上級報告,說他們逮住了「二十八個畜生」,請求派人前來支援。
「我知道漢人看不起藏人。但是,親耳聽他們把我們叫作畜生,心裏就像被紮了一刀。我衝上去,搶那個大兵的槍——死也要讓他把那句話收回去… …. 。」藏人青年如是對金聖悲說。
當時,二十八個流亡的藏人一擁而上,制服了五個士兵。士兵嚇得像「快凍死的羊一樣發抖」。藏人青年用槍口對準那個士兵的嘴,但終於沒有開槍。「我們沒有殺死大兵。只把槍帶走了,怕他們用槍打我們。沒有殺他們,不是不該殺——他們殺死好幾個尼姑。可我們是要到達蘭薩拉去見達賴喇嘛;我不能用染上人血的手給尊者獻哈達。」——藏人青年這樣結束了他的講述。
一位住在中國境內的七十多歲的漢族老人,給金聖悲講述了他平生最危險的一次經歷。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這位老人當時是中共軍隊的一名士兵。他所在的部隊進藏「平叛」,即鎮壓那次藏民大起義。他和他的偵察班,還有兩隻軍犬,追逐翻越雪山的藏人時,圍住了一個康巴女人。
「這個康巴女人又高又壯,跟一顆大松樹似的,腦袋比氂牛頭還要大。她用藏刀搏殺起來,就像藏廟裡喝醉酒的護法神。她一邊搏殺,一邊大笑,笑聲把人的心都能震碎。我們班的八九個兄弟都被她砍倒。她受的傷也不輕,流出的血把她的藏袍滲透了——浸血的藏袍沉得連大風刮過都不會飄擺。可她就是不倒下,好像殺不死的神靈。… … 兩隻軍犬狂咬她的小腿,腿上的骨頭都露出來了。可她根本不理睬狗,還用左手舉起酒壺喝了幾口酒,然後一刀就把我的軍帽劈掉。我的臉就露出來了——是我的這張娃娃臉救了我,我當年已經二十多歲,可從臉上看就像只有十四、五歲。康巴女人可能把我當成小孩子,猶豫了一下,沒有劈第二刀。我抓住機會向她開了一槍,在她脖子上射開一個血洞。康巴女人倒下之前,還對我伸出左手的小指,露出瞧不起的神氣。她死前的最後一個動作,竟然是用藏刀在她小腿露出的骨頭上敲了一下。她為什麼這樣作——是要聽刀和她的白骨撞擊的聲音嗎?我一輩子都沒有想明白這個問題。」——老人衰朽的聲音中滲出一片困惑,結束了他的講述。不過,即便是困惑,也喪失了生氣,像暗灰色的落葉,似乎他的心早已乾枯。
一位消瘦如岩石的老婦人,用佛殿中酥油燈的金焰般寧靜的語調,向金聖悲講述了她孫女的情與死。她的孫女生長在雅魯藏布江邊,從小痴迷於遙望金霞覆蓋的雄偉的大雪山。十六歲時,偶爾看到一張大寶法王的像之後,她就發下誓願,要作大寶法王眼睛裡的紅杏花。為實現誓願,她由老婦人陪同,沿大寶法王流亡的路線,走向喜馬拉雅群峰;她相信,只要她能同英俊壯麗的大寶法王逼近地作瞬間對視,她的容顏就會永遠怒放在法王蒼天般的眼睛裡。然而,翻越雪山時,她一邊的臉被嚴重凍傷。雖然到達了達蘭薩拉,她卻不能去見大寶法王,實現誓願。因為,她已經不能再盛放如紅杏花了——她一邊的臉依舊容顏如花,另一邊臉卻肌肉乾枯,猶如鐵鑄的骷髏。於是,在大寶法王駐錫的上密院外默禱一夜之後,她一個人重新走進藍天之上的喜馬拉雅雪山。她要化為一縷永不超生的剛烈的鬼魂,佑護那些翻越雪山的流亡者,直到藏人不必再踏上艱難的流亡之路。
「在這個真情枯竭,心靈荒涼的時代,情感豐饒、心靈繁富的藏人,意味著生命的奇蹟。藏人遺落在流亡之路上的悲情或者熾烈,或者艶麗,或者優美,或者深沉,或者燦若金霞… … 半個多世紀累積的豐饒的悲情,乃是蒼天都難以承受的心靈之重。如果生命的深遠處沒有英雄的風格,藏人不會比蒼天更堅韌。是的,西藏高原本來就是屬於英雄的國度。」金聖悲在思想中離開岩洞,再次開始漫遊。他的思想,則踏著雪山的峰脊走上蒼穹之巔,俯瞰西藏高原。
亞洲中部有一個萬山匯聚的山結,帕米爾;鐵黑色的帕米爾,是西藏高原的命運之結。幾道形如遠古的狂濤巨瀾般的山脈,以帕米爾為起點,扇形展開,向東方奔騰而去:東南方是洶湧在印度次大陸上空的喜馬拉雅峰海;中部依次是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脈、喀喇崑崙-唐古拉山脈和壯麗的崑崙山,東北部是橫亙在古絲綢之路蒼天上的阿爾金-祁連山。這幾條偉大的山脈經過萬里奔騰之後,在遼遠的東部突然被橫斷山脈的深峽截斷——西起帕米爾山結,南以喜馬拉雅為界,北以祁連山為疆,東以橫斷山為限,這是上蒼為西藏高原界定的自然疆域。達賴喇嘛心中的西藏高原恰好與上蒼的界定一致。儘管中共強權用政治的鐵手割裂了西藏高原,並指斥達賴喇嘛提出所謂「大西藏」的概念。但是,歷史將證明,上蒼的意志比任何政治意志都更接近永恆;自然的界定比強權政治的意志離人性的真理更近。
西藏高原是最偉大的山脈縱酒狂歌的王國。高原之上,鐵黑色的山體托起銀白色的群峰,綿延萬里。其中格外陡峭的山峰,有的像遠古英雄激情的殘跡,有的如同從大地深處沖騰而起的銀火焰,有的似湧向蒼穹之巔的龍捲風;其中特別雄偉的山峰,或者像王者的壯麗陵墓,或者如大海的雪浪托起的勇士的戰盔,或者似鷹王和萬里長風居住的金殿。暮色蒼茫或者晨光清新之際,萬座冰峰彷彿激盪在雲端之上的雪水河,那裡正是紫色的落日和金色的朝陽沐浴淨身的地方。
金聖悲每次漫遊西藏,都會為同一個信念而沉醉:只有英雄的壯麗命運,才配在這片高原上展開,而藏人正是西藏高原的選民。這不僅是因為藏人的心臟比低地的人更大,更強悍,所以適於高原生存——金聖悲並不關注這個,關注生理特徵是醫學家的事;作為詩意如花的哲人,金聖悲之所以確信這片高原是上蒼為藏人選定的家園,完全在於藏族男人的形象最適於表述英雄人格之美。
衛藏的男人像鐵鑄的鷹,消瘦,但又敏感而銳利,清秀的氣質中蘊涵著勇猛的神韻。安多的男人,頭顱碩大,如岩石雕成;神情端莊、安詳、遼遠,令人想起暴風雨之後的荒野;他們彷彿總在遙望的眼睛深處凝結著剛強的意志,即便天塌地陷、太陽破碎,那男兒的意志也不會崩潰。不過,安多男人雖然形容粗獷,但很多人卻格外精心地修飾自己的鬍鬚:上唇的鬍鬚形如兩枚修長的柳葉,下巴上的鬍鬚則像西藏藝人畫美女的毛筆的筆端。岩石一樣的男人竟把自己的鬍鬚變成藝術品,也是一種英雄的詩意吧。
喜馬拉雅是萬山之王,康巴鐵漢則是美男子之冠——那是壯麗輝煌的雄性之美。康巴男人,身形魁梧雄烈,縱酒高歌似懸崖起舞,昂視闊步如風暴臨空;青銅色的面容刻出英俊猛獸的威嚴,黑得炫目的濃髮間纏繞著紅綢,像燃燒的雲霞,像英雄之血的火焰。康巴男人,鼻如陡峻的山脊,眉似舒展的鷹翅,眼像彩鳳之目;他們的雙唇,輪廓俊美,形態豐饒,色澤深紅猶如總在深情地親吻火焰。當他們啟唇一笑時,白齒閃亮,那雙彷彿要看到人心底裡的眼睛深處,會猝然湧現出燦爛的善意——康巴鐵漢的笑能感染頑石,能讓少女的骷髏喜淚盈框。
「鼻塌眼濁、腿短腰長、身形猥瑣、神色低俗的南中國漢人,竟然也會從人種的角度蔑視藏人,那真是一種荒謬:鼠輩什麼時候也獲得了嘲笑壯麗猛獸的勇氣?」金聖悲長嘆如風。他堅信,藏人的天職就在於書寫英雄史詩;藏人之美就在於表述英雄史詩的遺囑。
「崇尚英雄的情懷,構成高貴而偉大的族群的生命標誌。沒有崇尚英雄情懷的民族,只是歷史地平線上轉瞬即逝的煙塵,沒有誰會注意那種瑣碎的存在。命運只會在時間的墓碑上,為英雄的族群刻出鐵石的花環,以志尊崇。」金聖悲追隨浩蕩的風,走進遠古的歷史;在時間的深處,他可以用自己那顆紅焰之心,親吻英雄的血——那像深紅的晚霞漫過鐵褐色大地的英雄之血。
在民族歷史的少年時期,藏人就以鐵血英雄的意志,征服了遠古的死寂與荒涼,成為這片離蒼天最近的高原之上的王者。以王權作為政治標誌的歷史中,圖博成為雄踞於世界之巔的強大帝國。當時的西藏高原是輝煌的雷電、浩蕩的風暴和雄烈激情的王國;藏人的戰刀和鐵騎時常如蒼穹之巔的太陽中迸濺而出的野性,從九天之上飛降而下,直擊低地的大唐帝國。藏刀上流光溢彩的鐵血戰志,迫使華貴的大唐皇室不得不向藏人之王獻出美女,以求苟安。
華美絕倫的古中華文化是金聖悲精神的故鄉。不過,中華文化史中也常有令金聖悲黯然神傷的篇章。其中恥辱至極的,莫過於在強敵前用女色換取苟安的傳統。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女人,本就是男人的原始恥辱——那是必須用血雪洗的恥辱。為苟安而向強權獻出自己的女人,則意味著血也洗不去的恥辱。那種男人只配用女人的內褲蒙面遮羞,渡過殘生。然而,中國男人的無恥還不止於此。中國的歷代政客和文人竟然把出賣女色以求苟安的鼠輩醜行,描繪成傑出的政治戰略;女人的色相換來的和平也被說成漢人的民族榮耀和歷史功績。墮落至此,太陽如若有情,定然也會羞慚得自溺於太平洋中,不再升起。中共的御用文人則更把歷史的恥辱演繹為現代的無恥:即便鬼神也難以想到,他們會用唐皇被迫出賣公主,即所謂「和親」的史實,作為「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謊言的論據之一。
「真實地面對恥辱,還有重新走向榮耀的可能;用謊言來修飾恥辱,則意味著人格的腐爛… … 。」金聖悲直視中國男人的骯髒與腐爛,竟然開始厭惡相關的思想;他甚至想剜出被弄髒的雙眼,用雪水河洗去眼睛上的污跡。
大約從佛教被奉為國教起,暴風雪停息了,藏人大海般動盪的靈魂寧靜了;西藏高原漸漸不再以雷電點燃的歷史表述英雄意志,而開始用佛的沉思追尋心靈。有的研究者為此而困惑,他們看不清動盪與寧靜之間的命運邏輯。其實,只要超越形而下的瑣碎繁雜,達到形而上的明澈,邏輯就會清晰地浮現出來:所有邏輯的起點都在於蒼天賦與西藏高原的神韻。
雪線是生與死的界限。雪線以下的高原之美屬於生命;雪線以上的那超越生命的美,屬於虛無——西藏高原本就是屬於詩和哲理的王國。英雄時代吟頌生命之詩,佛的時代進入哲理。佛最深遠的意境中呈現出的,正是純淨而聖潔的虛無的哲理和悲憫天下蒼生的心靈。
像一團團火焰般在鐵鏽色的荒野上漫遊的絳紅色僧衣,取代藏刀和野花,成為藏人美男子的象徵——這個歷史的轉變,具有超出藏人命運的意義。雪域高原,地球之巔,由超越物慾的信仰來管理,或許是一種天啟的宿命;這個宿命與人類的生存和心靈的救贖直接相關。
西藏高原的雪山和冰川構成東亞和中亞的萬河之源。從雪域高原奔騰而下的條條河流,養育了神州大地的古中華文明、南亞次大陸的古印度文明和東南亞半島的文明。近現代的個人私利至上哲理和縱欲生命觀中湧現出的生活方式,已使人類生存的自然背景遭到嚴重摧殘。如果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態由於追求物慾的生活方式而崩潰,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將蒙受毀滅性的災難,那或許就意味著古老的末日預言的實現。
由佛學信仰,即物慾淨化後的心靈,來主宰雪域高原的命運,不僅會使萬河之源免遭瘋狂物慾的荼毒,為人類保留一片淨土,而且在物慾中腐爛的人類,也可能從全民信教的藏人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中,得到精神救贖的啟示——幸福不在物慾中;心靈的寧靜才是幸福的源流。
然而,中共強權暴政卻逼迫藏人走上流亡之路。這不僅是中國的罪惡,東方的罪惡,也是西方的罪惡。因為,中共強權政治理論之魂,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源自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現代經典。中共鐵血強權迫使中國接受唯物主義。中共,這個只相信物慾召喚的政治動物,已經通過所謂經濟開發,開始毀滅西藏高原生態平衡的進程。同時,中共也在用屠殺和政治迫害,以及物慾誘惑,使藏人離開佛學信仰,並背叛心靈。佛學乃是雪域高原的文化之魂,如果魂被摧殘了,萬河之源也將變成毒氣污水之鄉,山崩地裂之野,就如同中國的萬里河山正在因為人的貪慾而經受的可悲命運。
很久以來,一份規劃在中共高層政客和御用文人中廣泛傳閱。規劃名稱叫作《大西線工程》,其主要內容是大規模引導西藏流向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的重要水流改道,轉向中國北部,解決華北和西北部分地區水源枯竭的危機。這個與自然邏輯相悖的瘋狂規劃一旦實施,必然引發地球循環系統失衡;可以預見,人類生態危機將成為規劃實施的悲劇性表述。同時,為爭奪水源而爆發世界戰爭將不可避免;人類會再次回到萬年文明史之前的荒蠻的起點——道德、良知、理性等等所有這些文明的法則都失去作用之後,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定然成為萬法之王。
《大西線工程》是一種瘋狂的非理性。不幸的是,它很可能再次取代理性,主宰雪域高原,乃至人類和地球的命運。因為,所有極權者或者寡頭集團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和實施戰略決策的高度理性。
兩線作戰是兵家大忌的非理性決策,但是,希特勒就以出乎所有戰略家之意料的兩線作戰,將二次世界大戰推向慘烈的極端;二次大戰時,連日本軍閥都根據理性分析得出結論:由於經濟能量的差距,日本同美國開戰將必敗,然而,日軍依然奇襲珍珠港,向理性發出鐵血挑戰;當年,幾乎所有的美國軍事專家都認為,裝備低劣的中共軍隊不可能入韓作戰,因為,那違背理性的權衡,可是,中共的實際行為卻羞辱了美國軍事專家的理性和智商。
與之同時,極權者戰略決策的執行卻又充滿沉靜到冷酷程度的理性。無論德國的閃電戰、還是日軍奇襲珍珠港的戰術安排,或者彭德懷的大縱深穿插推進伏擊的戰法,其理性設計都精確得像瑞士的鐘錶。極權者戰略執行過程中的絕對理性,正是其戰略決策非理性的效能倍增器,它可以使非理性的戰略決策迅速進入歷史,並摧殘人類的命運。
極權者都是精明的蠢貨:精明在於政治權術和陰謀,在於應對現實危機的機巧;愚蠢則在於對自然精神的宏觀蔑視,以及其對心靈的無知。中共極權者由於崇拜唯物主義而更是如此。所以,除了戰略決策的非理性特點之外,中共當局也很可能在現實危機的逼迫下,實施《大西線工程》。以毀滅性開發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經濟非理性發展,已經使中國北方生態系統進入崩潰程序,沙漠化的趨勢與水資源的枯竭齊頭併進;十年之內,中國將出現數億生態難民。如果中共極權還能生存得足夠長久,它就只能通過把雪域高原的水大規模引導向北方,解決直接威脅其專制政治生命的生態難民危機。對於中共極權,維護其政治存在是最高意志;它根本不在乎這種飲鴆止渴、割肉自啖式的作法對人類意味著什麼,它的全部聰慧就在於用一個更嚴重的罪錯,彌補原來的罪錯。
事實上,中共早已經通過濫採礦藏和在河流上大量筑壩,拉開徹底毀壞西藏高原自然邏輯的序幕。直視高原未來的自然命運面臨的困境,才能理解達賴喇嘛尊者關於把西藏建成世界和平區建議的慈悲之心。源自佛學的和平理念,既意味著對人類之間戰爭的否定,也意味著人對自然邏輯的尊重。只有一個在聖潔的佛學中沉思心靈的西藏,才能避免出現一個因物慾追求而瘋狂的高原——如果世界之巔由於物慾的瘋狂而失去理性,人類的歷史定將在非理性中萬劫不復。
「尊者已經把真理告訴世界,人類卻缺乏理解並實現真理的能力。一旦佛光隨最後一次落日的紫霞從雪域高原上消失,西藏將進入永恆的長夜,萬座瑩白的冰峰雪嶺會由於物性貪慾的侵蝕,而變成枯黑的真理的墓碑… … 。」金聖悲的思想走上了斷崖,他又一次悲哀地感到了真理的軟弱,同時也感到了實現真理的責任和希望:「實現真理是為了得到心靈的安寧,而實現真理的希望也正在於心靈——藏人心靈的力量。是的,真理的希望在藏人的心靈間棲息,藏人同中共的全部衝突,都集注於對待心靈的態度。」
毛澤東曾經對達賴喇嘛說,佛教害了藏人。他的意思可能是,藏人強悍的鐵血意志和野性銳利的生命風格,由於佛學而變得柔軟,變成一種心靈的沉思,因而喪失政治和軍事強者的歷史地位。
然而,毛澤東是愚昧的——這個物性世界中的權術大師,朦昧於心靈。人從自然邏輯中脫穎而出,獲得獨立於萬物之上的意志的命運,獲得以審美激情表述宇宙精神的權利,全在於人的本質是心靈的存在。朦昧於心靈者離人的本質比有限離無限更遠。毛澤東沒有能力理解,進入佛的意境之後,藏人雖然失去了政治和軍事的強大,卻在更深沉的意義上變得強大,那是屬於心靈的力量。
在半個多世紀中,中共暴政用滔天的血海、蔽日的軍刀和十萬鐵牢,都不能滅絕藏人的信仰,不能阻絕藏人的流亡之路——這是藏人心靈強大的證明。不過,當人類整體都因為迷醉瘋狂的物慾而喪失生命意義的靈性時,在一個背叛心靈之美的時代,藏人由於忠實於信仰而承受青銅色的苦難和冷酷的死亡,則是心靈強大的更經典的表述。
數十萬踏上流亡之路的藏人,沒有一個是基於追求物慾或者世俗利益,使他們從容承受命運艱難的原因,只在於心靈或者精神:法王流亡是為接近中共不准返回故鄉的佛學上師;僧人流亡,是為撕裂極權鐵幕,聆聽真實的佛法;詩人流亡,是為自由的吟頌;像高原的風或者草木岩石一樣自然的普通藏人,最具感動歷史的魅力,他們只是為了能來到達賴喇嘛的身邊而萬里流亡——那種虔誠的宗教感情並非世俗意義上的個人崇拜,而是心靈對佛的精神的皈依。
政治奴隸無真情。實際處於中共暴政政治奴隸地位的中國人和偽自由知識份子在嘲笑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感情時,他們應當知道,諸如他們一類喪失了虔誠的情感能力的人,不過是一個個謊言化的生命;謊言沒有資格嘲弄虔誠——如果他們不知道,那麽他們便比謊言更可悲,也更猥瑣。
金聖悲訪問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村的學校時,遇到過一位小女孩。女孩來自雪域高原的拉卜楞寺,今年已經十多歲,讀初中的課程。她的父母在她五歲時,託人把女孩帶到達蘭薩拉,目的是為讓她學會藏文。女孩向金聖悲展示一篇她用藏文寫的文章。那一行行藏字形態優美,宛似迎風翩翩起舞的思念。
女孩長得健康而飽滿,猶如一枚多汁的野果;眼睛純澈得像融化的高山之雪。儘管初識,她卻把心中最關注的事講給金聖悲聽——女孩依然相信人這個概念。女孩講,當年是一位小哥哥背她走到尼泊爾的;翻越雪山時,她的圍巾被風刮走了,小哥哥把自己的帽子給她戴,耳朵因此被凍傷。女孩來到達蘭薩拉的西藏兒童村之後,那位小哥哥一次也沒有來看望過她。有人告訴她,小哥哥不來看望,是因為凍傷的耳朵後來掉了——他不願讓她看到自己沒有耳朵的樣子。
「我長大後,一定去找小哥哥。他在印度南方。」女孩說出一個誓言。
「到時你還能認出他嗎?」金聖悲下意識地問。不過他立刻就後悔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作為一個哲人,為什麼竟會關心如此形而下的問題,或許只是因為他太希望女孩長大後能找到那個「小哥哥」——人世間美情感的結果常是悲傷與哀愁,而他希望女孩成為少女後,眼睛裡能閃耀起無盡的喜悅;他堅信,在女孩的心靈和眼睛裡,沒有耳朵的「小哥哥」都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兒。
「這不用擔心,我一定能認出他來。」女孩很快回答:「不過不是認出他的臉… … 我都忘了他的臉是什麼樣子,但我能認出他的背面——認出他的脖子和腦袋後面的頭髮。逃出來的時候,他每天背著我,有二十多天,整天我都看著他的脖子後面和頭髮。現在,我有時會記不住我自己在鏡子裡是什麼樣,可我忘不了他的脖子和頭髮… … 他的脖子後面中間有一個像小米那麽大的黑痣,頭髮上有兩個旋。」
女孩眼睛裡忽然淚影晶瑩;金聖悲震驚地發現,女孩的淚影竟然呈現出青銅色。「女孩的眼淚應該像花露一樣清香而流光溢彩。她的淚影為什麼會是青銅色?那是多麼堅硬而又哀傷的色彩呵… … 。」金聖悲在困惑中離開了女孩。他不知道自己應該被什麼感動——是女孩對「小哥哥」晨霧般迷茫而淡紫的純情,還是女孩父母對藏文化的深情。像女孩這樣從小就被父母送到達蘭薩拉學藏文的男女兒童有許多。父母的心堅硬到怎樣的程度,才會把孩子,自己身上掉下來的骨血,送上艱險莫測的萬里流亡之路,送進暴風雪瀰漫的命運之旅。而比他們的心更堅硬的,乃是一個族群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苦戀和對精神故鄉的忠誠。
半個多世紀的迫害、酷刑、屠殺和誘惑,卻不能改變藏人靈魂的風格。高原的酷寒能凍裂鐵鑄的心,可凍不裂藏人的信仰;藏人的心靈就是刻在氂牛頭骨上的彩色經文,高原的風能吹裂頑石,可吹不裂潔白如雪山的氂牛頭骨。當前,世界各國多如印度夏日之蠅的政客、商人、文人,服從世俗物質的誘惑,以種種猥瑣的姿態,在中共極權前爭寵獻媚。在這精神艱難的時刻,藏人只為心靈的原因,而用胸膛與中共強權的屠刀抗爭。這種「孤獨」,正表達心靈的強大。
「心靈常常受到物慾的嘲笑,因為,歷史總在物慾的誘惑下,進入庸俗、污穢、墮落的時代。這一切似乎在證明唯物主義的結論:人本質上是一堆灼熱的物慾;物慾是主宰歷史進程的王者。不過,在命運的關鍵之點上,心靈會以聖潔的信仰和激情,引領人類走向高貴與美。之所以如此,或許基於一個精神哲學的信念:人本質上是‘追求意義的動物’;意志的歷史最終要聽從心靈的召喚… … 。」
金聖悲在思想中漫步,他看到,藏人翻越喜馬拉雅的白骨與紅血之路,伸展向時代的精神之巔;藏人正在由於對心靈的忠誠而感動歷史,當人類有一天從物慾的黑暗中仰視蒼穹,尋找啟明星時,會從藏人苦難的心靈史中看到精神的希望。中共暴政不會想到,它把藏人逼上流亡之路,而那條離開塵世中的祖國的路,既是重歸心靈的故鄉之路,也是走進人類歷史中心的光榮之路。暴政在用浴血的苦難,為藏人編織值得供奉在太陽之巔的榮耀的花環。
金聖悲紅焰的心在熾烈的疼痛中震顫,那是只有用關於英雄的思想才能撫慰的疼痛。於是,他在烈焰的疼痛中開始了思想:
「藏人的流亡是當代的英雄史詩。半個多世紀抗爭的意志,既來自心靈信仰,也源於古老的英雄人格。藏人的歷史從英雄時代進入佛的時代之後,英雄人格卻並沒有凋殘,就如同銀白的冰峰上,金色的霞影在每個日落時依然重現古老的燦爛。值此中國文人中自命自由主義者的小男女惡毒詛咒英雄的時刻,西藏高原仍然堅守對英雄的敬意。格薩爾王傳奇,那隨搖搖滾滾的風在鐵褐色大地上四處漂泊的游吟詩人傳唱的史詩,正是藏人生命風格的表述。游吟藝人相信格薩爾是佛學大師蓮花生轉世——這證明在藏人的靈魂中,詩與哲學凝成同一顆情感的露珠;英雄人格和慈悲的佛理共同托起格薩爾傳奇,這人類英雄史詩之王。稱格薩爾傳奇為英雄史詩之王,並不是由於它的篇幅比所有的史詩漫長——再長也沒有時間長;也不是由於它的詩意豐饒如海——世界上每一篇史詩都有獨特的美色,而是因為所有民族的英雄史詩都早已成為歷史廢墟中的墓碑,成為文化考古的對象,而格薩爾傳奇仍然活在藏人的靈魂深處,活在西藏高原荒涼而美的地平線上。英雄史詩因藏人的靈魂和雪域高原而不死。」
思想重歸英雄人格的意境,使金聖悲生機盎然。他一直把英雄人格和美設定為他哲學的主題;此刻他發現,英雄人格和美也是藏人生命的主題。他曾欣賞過一幅西藏工筆畫藝術風格畫出的格薩爾王的形象。畫面上,格薩爾王正縱馬奔騰在彩雲之端。他的坐騎是紅得比火焰還艶麗的雄馬,馬的體形宛似飛奔的猛虎;格薩爾金盔銀甲綠帶,手執戰旗,追逐雷電縈繞的太陽。整個色彩繁富的畫面激盪著狂風怒濤般的動感,顯示出屬於雄性的壯麗與華貴,強悍與輝煌。就在看到那幅畫的最初一刻,金聖悲感到,在審美激情的意義上,他同藏人之間似乎有某種古老的心靈默契。
鷹群的鐵黑色長翼劃傷了藍天,被藍天之血染成紫紅的流雲,縈繞在金聖悲身旁,引導他來到一座山峰旁。岩石的峰頂呈現出鉛灰色,破裂的岩體極其陡峻,就像烈馬狂奔前的瞬間機警聳起的耳朵。山峰中部岩洞外的陡坡上,是格薩爾王和他的十幾位將領的墓。一條峰脊從右邊圍繞住墓群,如同陡峰的手臂護衛著英靈。
陵墓形如一座座白銀鑄成的戰盔,墓群周圍的岩壁滲出淡淡的枯紅,像遠古的血跡,那正是適於哀悼和沉思英雄的色澤。金聖悲背倚格薩爾王陵的墓基,盤膝端坐。他根本不在乎關於格薩爾是真實的存在,還只是傳說中的人物的爭論;對於他,知道格薩爾史詩的英雄人格是藏人靈魂的真實內涵就足夠了。他堅信,墓群下埋葬的定然是雷電和狂風般的英雄男兒的遺體,而格薩爾王墓下埋葬的則是金色落日的骸骨。
從金聖悲端坐之處望去,對面的山坡上有幾株杜鵑花樹。此處的杜鵑花呈現為藍白色,可是怒放的花形卻風格繁富——淡雅的色調與繁富的花形構成一種醉人的美感,彷彿純潔的藏族美少女對英雄的迷戀。
杜鵑花樹隨藍色的風搖曳生姿,使金聖悲的思想飄搖在詩意之中,難於進入哲學意境。大野寂靜,英雄格薩爾的陵墓向怒放的杜鵑花的永久凝眸中,似乎湧現出與彿學哲理一致的生命美的意境。金聖悲的眼睛格外明亮地閃爍了瞬間,而他的思想比眼睛更燦爛:「難道我已經找到了藏人之魂?在寧靜至極的寂滅和滿月般晶瑩的虛無——那佛的精神背景上呈現出的英雄人格和招搖的杜鵑花的花枝,便是藏人靈魂的象徵。明知終將歸於寂滅,神形俱消,也要在短暫的生命中堅守心靈的信念;明知命運終將化為虛無,也要用英雄人格和花枝表述對瞬間的生命之美的崇敬與忠誠——這便是藏人的魂嗎?」
不過,金聖悲的眼睛很快又變得蒼茫了。他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找到藏人的魂。因為,他紅焰的心依然沒有熄滅;紅焰中,梅朵依然在作妖嬈而苦痛的焚身之舞。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個聲音告訴他:「藏人的魂比你想的離自然更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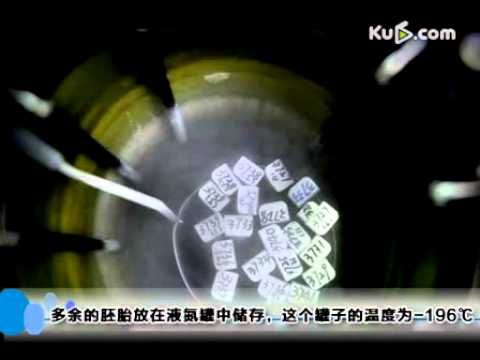









排序